ciao
@ciao
ciao
@ci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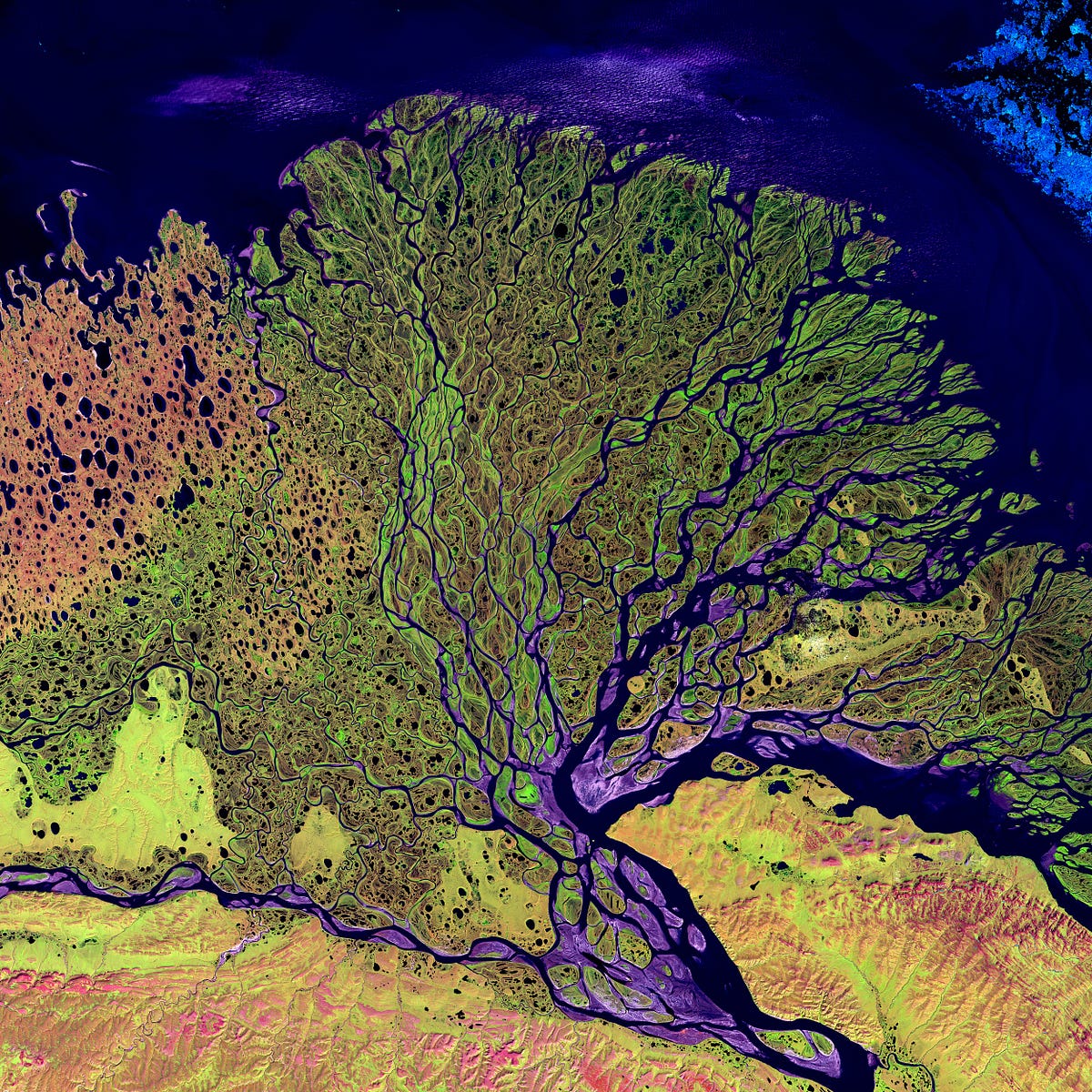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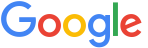
所謂的整理,不是只是打掃乾淨或清掉多餘的物品、而是根據這個人的生活習慣,歸納出專屬於他的整理系統。處理遺物的過程,也不是處理家人,空間乾淨了,過往的日子方可以安心回憶。不要讓空間的沉重感和低能量,讓你成為一個無法停泊的人。
遺物,最終只是物品。把自己想要的東西留下,剩下的即便是逝者珍視的物品,那也與我們無關。最重要的是,我們曾經的回憶和連結,才是最珍貴的存在,因為只有我們能證明,我們的愛存在過。
寫到這,我以自己死了的視角問了自己幾個問題,也邀請你和我一起思考: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我現在的遺物好整理嗎?會不會為家人帶來麻煩?
那我現在有哪些是我已經可以整理的東西?如果我死了,它們其實不存在價值。
我有哪些習慣一直在為自己增添生活的重量、佔領空間?
如果我現在死了,我有哪些東西一定希望家人可以用特定方法處理?像是轉送某人?
比起想像他人的死亡,好像想像自己的死亡更讓我自在一些。因為我能夠改變自己活著的方式,卻改不了別人的,更對死亡最終會來臨的事實無能為力。
但又如何?我們所能夠做的,就是好好活著。
輔大生死學的李志成教授曾說:
「整理我遺物的人無法為我收拾人生,因為我的人生將隨我的逝去而終止。我們無法代替死者向生者做和解,死者已矣,死者也不一定要向誰和解,惟有生者可以以自己的形式和死者和解。」
我們要好好生活,不遺憾地來到生命盡頭。
好好活著,延續自己身上所有愛的交集,包括和逝者的。
我們都渴望和家人變得親密,同時也期待有自己的空間。整理遺物的過程,也是在練習和同住的逝者分出界線。你在你的世界,他去往他的彼方。
許多先進國家對於博弈事業的管理囊括了心理精神健康的面向,會編列特殊專屬財源或預算協助賭博成癮個案就醫。相較國外,臺灣對病態性賭博的研究與發展相當落後。現階段全民健康保險的給付對於具有社會爭議的行為不一定給予健保給付的價值,如用藥、單純戒毒行為、酒精成癮等,而這一定程度牽涉臺灣對精神醫療的污名化。
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謀弒母親、婆婆與丈夫
Reading hasn't changed much since Gutenberg. Sure, we've moved from paper to pixels, but we still primarily consume text linearly, making highlights and notes just as readers did centuries ago. We know active learning beats passive consumption. Yet reading remains mostly solitary and one-directional.
AI changes this equation. Instead of just
... See moreI have found more relief in demoting my mind and elevating my body than I have in my entire life. It feels so liberating to me, because, my entire life, I was desperate to be free from myself.
Bryan Johnson
And it became clear to me that the mind is not a reliable source of judgement.
學習語言之於我,總是探索而非精進。